忘了当时画的是什么金鱼图了。那时六岁,刚搬了家,脑细胞如初春枝头的灿烂繁花怒放,一发不可收拾,拿起笔来,就开心地临摹任何身边吸引我的图画。确实如此,六岁前我对画画是毫无意识的;六岁后忽然地我就萌生画画的冲动了,也不需要人教,也根本没人能教,就像鸟儿羽毛一旦丰满,自然渴望傲游天际。六岁那一年,我基因里的密码组合启动了画画的本能,这一生就此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。
开始作画都是靠模仿的。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母亲用来装针线的大白兔奶糖铁盒,雪白的大白兔,跃过几朵鲜红的野蘑菇,我照着画,心满意足。当然,还有交给幼儿园老师的那幅金鱼图,也是临摹抽屉里挖出来印在残旧皮夹子上的图案。不想这样的小图,竟然吸引了某个人的目光。某日,老师交给我一张书签,正面印着力争上游的三尾鱼儿,背后用蓝色钢笔写了几行字。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,拿回去给家人看,姐姐才说是某个黄姓大哥,喜欢我的那张金鱼图,索了去,回送书签,祝福我学业进步。
那是70年代末的事,不算久远,怎么却有几分朦胧的传奇色彩?有点眷念那个年代了,互送书签,遥寄卡片,不靠打字,而是手书几行寄语,仿佛把自己的呼吸注入笔迹里,一张平凡的纸片,就此活了起来,温暖着收件人的心。现在我们都不写信了,我们都逐渐淡忘,用书写的文字慢慢填满彼此间的距离,是多么实在而浪漫的生命美学。现在我们也不互送书签了,甚至连书签究竟为何物,恐怕年轻一代也不太在意了吧?
但我就是有一点食古不化的。我们不写信,手写明信片总还可以吧?数周前,配合我的工作坊,特地创作了一张布布怀抱大熊猫的小图,并将之印刷成明信片,打算送给参与工作坊的小朋友,留作纪念。而刚好又收到报馆送来的“话中有画”绘本创作亲子组参赛作品,每一本小书无论程度如何,都是小朋友用心之作,应当给予最大鼓励。于是就萌起给所有参赛小朋友手写明信片的念头。
我希望所有参赛的小朋友,都不要忘了画绘本时的快乐与满足。因为这份快乐与满足,是你的,别人拿不走。把几句简单的鼓励话语寄过去,我早已不是当年六岁画金鱼图的小孩子,原来我们都可以是某个孩子生命里的不相识的“黄大哥”。
黄大哥的书签这么多年来还留着,都已经泛黄了,他那一手蓝色钢笔繁体字,流露着70年代末华校生的俊逸,有一股飞扬的气势。我不知道他是谁,为何会到幼儿园要了我的图,我们根本没碰过面,生命不曾真正交集,但黄大哥那几行字,却如同陌生的老朋友,住进了我的生命;只是不知我的那幅金鱼图,而今是否还在他生命里悠游?
*附图为配合工作坊印制的明信片 “Say Cheese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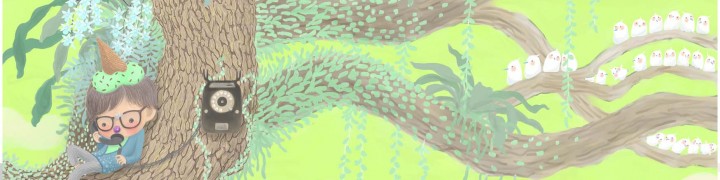



Leave a comment
Comments feed for this article